中戏教师带你解读段奥娟《岁岁平安》
百度云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n5xxv6t7ry6aRL5xT4Y644m
# 《岁岁平安》:血缘的枷锁与爱的救赎——一次对家庭本质的深度叩问
在中国家庭伦理叙事的长河中,“血缘”始终是一个沉重而神圣的符号。《岁岁平安》以一场由疾病引发的伦理危机为切口,却并未止步于对传统血缘观的简单维护或批判,而是进行了一场更为深刻的解构与重建。影片表面上讲述的是一个“为救儿子寻回弃女”的救赎故事,内核却是一场关于“何为家”、“何以成为家人”的哲学思辨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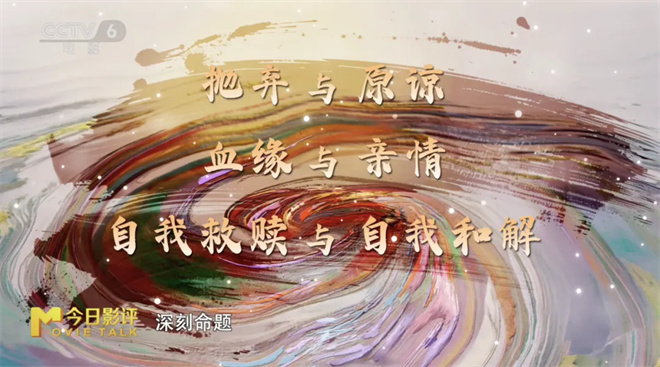
## 一、 “抛弃”的双重叙事:创伤的根源与执念的牢笼
影片的深层逻辑始于对“抛弃”这一行为的双重诠释。母亲李枚的抛弃,表面是十年前一个迫于生计的无奈选择,实则是父权制家庭结构下“重男轻女”观念的悲剧性缩影。然而,影片的深刻之处在于,它并未将李枚简单塑造为一个反面角色,而是揭示了她在传统观念裹挟下的困境与后续漫长的自我惩罚。她的“寻回”行动,既是救子心切的生物性驱动,又何尝不是一次对自身罪责的隐秘救赎尝试?
更具洞察力的是影片对“被抛弃者”岁岁内心世界的刻画。王楠老师分析的“伤痕时刻”——大巴车上身世被揭穿,其震撼力不仅在于真相的残酷,更在于它精准呈现了创伤的“延时性”与“重构性”。岁岁的震惊与恍惚,意味着她过往的自我认知与世界图景在瞬间崩塌。这处伤痕,远不止于被生母抛弃,更在于她赖以生存的“家”的叙事被突然篡改。这种深层的信任崩塌,构成了她内心冲突的根源。
## 二、 超越血缘:养父老刘与“选择成为家人”的伦理实践
养父老刘这一角色,是影片颠覆传统家庭观的关键载体。他的存在,彻底解构了“血缘即亲情”的必然性。他对岁岁的爱,是无条件的、非功利的,其动机源于纯粹的情感联结与道德责任。影片通过“一送一迎”的细节,升华了这种爱的本质:“送”是明知可能失去却仍尊重其寻找血缘的自主权,是爱中的放手;“迎”是无条件接纳伤痕累累的回归者,是爱中的坚守。
老刘代表的是一种“实践性亲情”——亲情并非由血缘预先注定,而是在日复一日的付出、关怀与共同生活中构建而成。他在隧道中听到“我养你”时含泪的微笑,正是对这种建构性关系得到确认的终极慰藉。他治愈岁岁的方式,并非抹去其创伤记忆,而是赋予她新的情感脚本:你值得被爱,且有能力去爱。
## 三、 “少年与子弹”的隐喻:与自我和解的终极命题
“不要用过去的子弹,射击未来的自己。”这一核心隐喻,将影片的主题从人际层面的原谅,提升至个体内心的战争。岁岁面临的最大敌人,并非生母李枚,而是内化了“被抛弃”命运的那个愤怒、悲伤、自我怀疑的“内在小孩”。捐献骨髓后选择回到养父身边,这一行为的深刻意义在于:它并非对生母的原谅(影片也并未强行达成此和解),而是**与自我的和解**。
她放下了“必须恨”或“必须原谅”的执念,停止了用过去持续惩罚现在和未来的精神内耗。她接纳了创伤是自己历史的一部分,但拒绝让其定义自己的全部身份与未来。这种选择,是一种充满主体性的宣告:我的人生叙事,由我主导;我归属的家,由我选择。
## 四、 段奥娟的表演:作为叙事载体的身体与情感
段奥娟获得赞誉的表演,之所以成为影片的“惊喜”,恰恰因为她精准地外化了上述复杂的内心进程。她的表演不是情绪的简单宣泄,而是层次分明的“内心地貌图”。从大巴车上的茫然失重(创伤的瞬间冻结),到后续与生母相处时的疏离与暗涌(情感的矛盾挣扎),再到隧道拥抱养父时的坚定与温暖(新主体的诞生),她的身体与微表情成为了叙事本身。
这种表演的“质感”,让岁岁的转变避免了说教般的突兀,而是让观众在情感的沉浸中,信服并共鸣于她最终的抉择。段奥娟的成功,不仅是个人的突破,也证明了年轻演员完全有能力驾驭复杂伦理剧的情感深度,这为中国电影表演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## 五、 行业意义与社会回响:一次对家庭叙事的范式革新
在充斥着狗血冲突或廉价温情的家庭题材影视市场中,《岁岁平安》提供了一种更为克制、深邃且现代的叙事范式。它没有提供“大团圆”的廉价解药,而是呈现了一个充满伤痕但最终走向平静与自主的结局。这呼应了当代社会越来越多“非传统家庭”(如重组家庭、收养家庭、选择不婚不育的亲密共同体)的情感现实,探讨了“心理家庭”与“法律/血缘家庭”并不总重合的普遍困境。
影片最终给出的答案振聋发聩:**家庭的真谛不在于你从何而来(血缘),而在于你被如何对待(爱),以及你选择与谁共筑归属(选择)。** 原谅不是家人的义务,爱才是成为家人的前提。这不仅是岁岁个人的救赎之路,也为所有在血缘枷锁与情感真实间挣扎的现代人,提供了一种思考与解脱的可能。
《岁岁平安》的价值,正在于它勇敢地刺破了“血缘至上”的神话,在废墟之上,用“爱”与“选择”重新奠基了“家”的意义。它告诉我们,平安的岁岁,终将属于那些我们主动选择去爱,并确信自己被爱着的地方。这,或许是这个时代最需要聆听的关于“家”的寓言。





